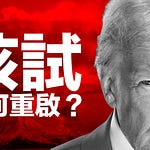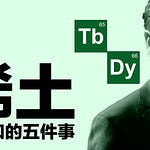我和大寶從美國與澳洲遠道而來,在臺北街頭進行一場跨越時區的實體交談時。一個問題即時浮現在我們的腦海:過去幾年臺灣一直在希望「讓世界看見臺灣」,從我們這些非本土的觀察者,究竟又看見一個怎樣的臺灣?
日式紀律與工作文化衝擊
從一個外來者的視角來看,臺灣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其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紀律與「程式化(SOP)」精神。這不僅體現在疫情期間對防疫流程的嚴格遵守,也貫穿在臺灣的企業管理與工作風格中。在辦公室文化中,無論是狹窄的空間佈局、員工的排排坐,或是主任坐在隊列後方的安排,都反映出源自日本的階層與群體協作模式。
這種紀律性為臺灣的經濟成功提供了穩固的基礎。臺灣同事以忠實執行指令聞名。只要管理者能提供極度清晰的指令,他們便能高效地完成任務。然而,這也帶來一個潛在的溝通挑戰:若指令不夠明確,臺灣同事傾向於順應而非提出質疑,這要求主管必須做到極高的溝通準確性。
這與我們習慣的香港文化形成鮮明對比:香港人在缺乏明確規範時,往往表現出變通性和嘗試突破的探尋精神;而臺灣人則更傾向於在既定框架內追求完美執行。對於來自海外的主管而言,與臺灣團隊的合作需要一個「磨合(Fine Tune)」過程,充分理解他們對清晰結構的需要。
海外臺人的影響力與經濟「黃金交叉」
除了本土文化,海外臺人社群對臺灣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無論是在美國西岸或澳洲,這些離散的臺灣人形成了強大的聯絡網絡。特別是在美國,當年因故離臺的社群,在臺灣的政治轉型和資源回流上貢獻良多。他們不僅帶回了資金,也帶回了國際視野和政治網絡。時至今日,許多科技巨頭如 AMD 和 NVIDIA 的核心領袖均具有臺灣背景,這已成為臺灣在全球科技界的代表。
這種全球影響力在當前的臺灣經濟中得到了印證。若單純以臺北核心區域的景氣來看,高漲的消費與物價、充沛的國際遊客(尤其是來自東南亞、泰國和香港的旅客)都顯示出經濟的活躍。這與臺股加權指數的表現形成了呼應。
從經濟史的角度回望,臺灣經濟或許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隨著全球產業結構轉向高科技製造和半導體,逐漸與傳統金融中心香港拉開了差距,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黃金交叉」。同時,當年備受質疑的「新南向政策」,如今看來,其對東南亞市場和穆斯林社群的包容與設施建設,已為臺灣帶來了可觀的區域紅利。
港人移居挑戰與無法取代的「人情味」
對於近年來考慮移居臺灣的香港朋友而言,儘管語言和繁體中文提供了極大的親切感,但門檻正不斷提高。無論是讀書或投資移民,臺灣移民署的審批流程比其他地區更具不確定性。
在社會運行上,臺灣看似講求「程式」,但其程式背後往往潛藏著一種無法被西方標準程序取代的「人情味」。在臺灣,辦事有時會出現「識人好過識字」的傾向,但這裡的「識人」並非香港傳統的裙帶關係,而是一種對於鄉親、族群身份的認同與互助,體現在對僑務活動的支持或節慶時的熱心幫忙。
這種人情味的展現,在社交場景中尤為突出。儘管臺灣的酒桌文化仍有「斷片式劈酒」,但與其他地方相比,其勸酒行為多是出自於熱情與友誼,而非強制性的階層壓力。這種情義也延續到職場之外,許多人即使離職多年,仍能與臺灣同事維持節日問候與互助的關係。
綜合這些觀察,臺灣正逐漸成為一個「離散香港人 Hub」。它不僅提供了與香港文化最接近的生活環境,語言上的「不鹹不淡」更是一種溫和的包容。在世界局勢變動的背景下,臺灣以其獨特的紀律精神和深厚的人情底色,為尋求新起點的香港人提供了堅實的立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