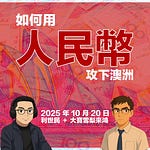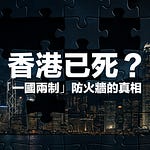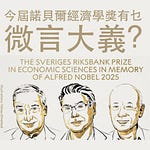權力與影響力的區別
「權力」與「影響力」是兩回事;權力是「迫使他人改變行為的能力」;當一個人或一個群體能夠強制他人去做他們原本不願意做的事情,這就是權力的展現。
影響力的作用於思想,能夠改變人們的價值判斷、信念和偏好。
理論上,思想可以不受強制而保持獨立。
但是當有人能夠同時控制權力與影響力,甚至乎以權力去建立影響力,這意味著統治者不僅可以決定人們的行為,甚至能操控人們的思想。這也是為何自由社會必須維護言論自由,使影響力可以在公開競爭中分散,而不至於與權力綑綁為一。
殖民時代香港的權力分立
香港作為殖民地,雖然沒有普選所帶來的民主。然而,殖民香港一直存在微妙的權力分立與制衡;而這個現象背後並不是源自於公民授權,而是因為殖民政府在治理上的實際需要。倫敦既不可能就每件事都鉅細無遺地向港府發施號令,也不可能掌握在地錯綜複雜的利益瓜葛和矛盾,最低成本高效的統治,就是透過在香港社會自行約束權力的行使,但此舉亦讓殖民地時代的香港建立出一種「免疫力」,避免權力過度集中而腐敗。
制度免疫系統的建立與失衡
1967 年暴動是香港統治的分水嶺;當時中共內部出現權力結構的全面崩潰,就連一直潛伏在香港的地下黨員也忽然躁動起來。雖然最後平息了風波,但是也改變了港英的管治思維。1970年代之後,教育普及、中產階層壯大,香港逐漸形成活躍的公民社會。報紙、專業團體、工會與學生運動。這個時代的所謂「認祖關社」也培養出一整代香港在各範疇的精英;雖然他們絕大多數缺乏直接的政治權力,但形成了「影響力的制衡」,這也是由社會力量構成,「香港制度免疫系統平衡」的寫照。
然而,香港的制度免疫系統在九七主權移交後開始轉變;中國的影響逐漸轉化為權力,並打破了原有的制衡。
若要理解香港制度的崩解,就必須回到 1999 年的一個關鍵事件:市政局與區域市政局的廢除。表面上這些機構掌管公共衞生與康樂設施,雖權力有限,卻是香港殖民時代殘留下來的「地方自治」痕跡,是香港特區唯一有權力自行決定預算分配以及指揮獨立行政機關的代議政制機關。特區政府以「精簡架構」為名,將之徹底廢除,實際目的是要消除在香港唯一議會主導的管治架構。
《基本法》當中沒有具體寫明有市政局與區域市政局的存在,也反映了北京其實早就定下香港必須以絕對的行政霸道模式管治。
至於「問責制」其實就是確立政府各機關首長,仕途取決於能否獲得中央確認,而非忠於官僚制度規章。
轉捩點:23 條
回歸初期,北京仍保持一定克制,但2003年50萬人走上街頭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徹底改變了局勢。北京驚覺:香港仍有能力挑戰中央意志,於是轉向全方位加強對香港的影響,同時逐漸收緊對香港的控制。
2003 年至 2019 年,是香港制度逐步瓦解越見表面化的十六年。由 2003 年反廿三條和倒董,到 2012 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2014 年的雨傘運動、2019 年的反送大,每一次抗爭都是香港社會「免疫系統」的自發反應。
然而,從北京的角度,那是「免疫系統」過份活躍,最後的選擇就是全面切斷香港本來的免疫系統和功能。
免疫力缺乏症下的香港
殖民香港沒有普選但有制衡,也構成香港的「制度免疫力」。然而,自北京將影響力轉化為權力,直至最終徹底摧毀制度平衡,香港不但失去了抵抗力,也失去了適應力,結果是必須「融入母體」(absorb into the mainland system),將自身抵抗和適應的功能,交由「母體」來指揮,這也是制度崩解最終的結果。